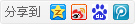第01章 一顆紅星的幼年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湘潭縣的韶山沖。我的父親(1)是一個貧農,當他年輕的時候,因負債累累,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2)。後來他回到我生長的村上,由於拼命地節省,他靠著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賺了一點錢,設法贖回了他的田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成為中農了。在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穫六十擔穀。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擔——這就是說,每人約七擔——這樣,每年可以多餘二十五擔。靠了這個剩餘,父親積聚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達到“富”農的狀態。這時,我們可以每年在田裏收穫八十四擔穀。
當我十歲,我家祗有十五畝田的時候,一家五口是: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們增加了七畝田之後,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和兩個妹妹。不過我們每年仍有三十五擔穀的剩餘(3),因此,我家一步步興旺起來了。
這時,父親還是一個中農,他開始做販賣糧食的生意,並賺了一點錢。在他成為“富”農之後,他大部分時間多半花在這個生意上。他雇了一個長工,並把自己的兒子們都放在田裏做工。我在六歲時便開始耕種的工作了。父親的生意並不是開店營業的。他不過把貧農的穀購買過來,運到城市商人那裏,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在冬天磨米的時候,他另雇一個短工在家裏工作,所以在那時他要養活七口。我家吃得很節省,但總是夠飽的。
我七歲起,就在本村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到十三歲。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裏做工。白天就讀《四書》。我的塾師管教甚嚴。他很嚴厲,時常責打學生。因此,我在十三歲時,便從校中逃出。逃出以後,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於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為那個城是在某處一個山谷裏面的。我飄流了三天之後,家裏才找到我。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過繞來繞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過距家約八裏。
但,回家之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點。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我這次反抗行為的結果,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我第一次勝利的“罷工[罷課]”(4)。
我剛認識幾個字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要我記家賬了。他要我學習打算盤,因為父親一定要我這樣做,我開始在晚間計算賬目。他是一個很兇的監工。他最恨我懶惰,如果沒有賬記,他便要我到田間做工,他的脾氣很壞,時常責打我和我的弟弟們。他們一個錢不給我們,給我們吃最粗糲的東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總給雇工是吃雞蛋和鹹魚片,但很少給過肉。對於我,則既沒有蛋也沒有肉。
我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麼都肯施捨。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不過在父親面前,她就不能這樣做了。他不贊成做好事。家中因了這個問題時常吵鬧。
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雇工也在內。不過,在反對黨的“聯合戰線”之中,意見並不一致。母親主張一種間接進攻的政策。她不贊成任何情感作用的顯明的表示,和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說這樣不合乎中國的道理。
但當我十三歲時,我找到了一種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親辯論,我引經據典,站在父親自己的立場上和他辯論。父親常(常)喜(歡)責(備)(5)我不孝和懶惰。我則引用經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為上的應該慈愛。至於說我懶惰,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年輕的人多做工作,而父親的年紀既然比我大上三倍(6),他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並且我說我到了他那樣大的時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這個老人繼續“積聚財物”,在那個小村裏可以說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買田,但是他向別人押來很多的田。他的資本增加了兩三千元。
我的不滿增加起來了。辯證的鬥爭在我們的家庭中不斷地發展著。[在說話的時候毛很幽默地引用這些政治術語,他一面笑一面追述這些事件——史諾(7)]有一件事,我特別地記得。當我在十三歲左右時,有一天我的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面前,我們兩人發生了爭執。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憤恨他,離開了家。我的母親在後面追我,想勸我回去。我的父親也追我,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個池塘的邊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點,我便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戰”。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並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這樣結束了這場“戰事”。從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當我以公開反抗來保衛我的權利時,我的父親就客氣一點;當我怯懦屈服時,他罵打得更厲害。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父親的苛刻,結果使他失敗。我漸漸地仇恨他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真正的“聯合戰線”來反對他。這對於我也許很有益處,這使我盡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記賬,讓他沒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能夠記賬。我的母親則完全不識字。兩人都出身農家。我是家庭中的“學者”。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時的傳奇小說,尤其是關於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輕時,我不顧教師的告誡,讀了《岳飛傳》[《精忠傳》]、《水滸傳》、《反唐》[《隋唐》]、《三國》和《西遊記》等書(8),而教師則深惡這些不正經的書,說它們害人。我總是在學校裏讀這些書的,當教師走過面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著。我的同學大多也是如此。我們讀了許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夠背誦出來,並且一再地談論它們。關於這類故事,我們較本村的老年人還知道得多。他們也歡喜故事,我們便交換地講聽。我想我也許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因為我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
最後我在十三歲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做長時間的工作,幫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著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然而我還繼續求學,找到什麼書便讀,除了經書以外。這使父親十分生氣,他要我熟讀經書,尤其是當他有一次,因對方在中國舊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適當的經書而使他官司打敗以後。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門遮蓋起來,使我的父親看不見燈光。我這樣讀了一本我很歡喜的書,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9)。該書的作者們都是主張革新的老學者,他們以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由於缺少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輪船等,並想將它們介紹到中國來。我的父親認為這一類的書是浪費時間的。他要我讀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的如經書那類的實際東西!
我繼續讀中國文學中的古傳奇和小說。有一天,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可注意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奇怪了兩年,於是我便進行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我發現這些故事都是讚美人民的統治者的武士,他們用不著耕種田地,因為他們佔有土地,顯然是叫農民替他們工作的。
在少年與中年時期,我的父親是一個不信神佛的人,但母親則篤信菩薩。她對自己的孩子們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九歲的時候,我便認真地和母親討論父親沒有信心的問題了。(10)自那個時候以及以後,我們都想了許多辦法來改變他的心,但沒有效果。他祗是責罵我們。因為我們受不住他的進攻,我們退而想新的計劃。但他無論如何不與神佛發生關係。
不過,我的讀書漸漸地對我發生影響:我自己愈來愈懷疑神佛了。我的母親注意到這一點,責備我不該對神佛冷淡,但我父親則不說什麼。後來,有一天,他出去收賬,在途中碰見一隻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驚逃,但我的父親卻格外地害怕,後來他對於這次奇跡的逃生,仔細想過。他開始想他是不是開罪了菩薩。自那時起,他對於菩薩比較恭敬起來,有時也偶爾燒香。但是當我愈來愈不信神佛時,他老人家卻並不管。他祗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向神禱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1)引動我繼續求學的欲望。我也已經厭恨田裏的工作了。這自然是父親所反對的。我們為了這事發生爭執。最後我從家庭中出走。我到一個失業的法律[法科](12)學生家裏去,在那裏讀了半年書。此後,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讀了更多的經書,並讀了許多當代論著和幾本書。
在這時候,湖南發生一樁影響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們讀書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們一班同學看見許多從長沙回來的米商[豆商](13)。我們問他們為什麼大家都離開長沙。他們說是城中發生了大亂子,並把這件事告訴我們。
原來那年發生一個大饑荒,在長沙有好多萬人沒有東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舉了一個代表團去見巡撫,請求救濟,但他卻傲慢地回答他們:“你們為什麼沒有糧食?城裏多得很,我向來就沒有缺少過。”當他們聽到巡撫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憤怒。他們召集民眾大會,舉行一次示威運動。他們攻進滿清衙門,砍倒作為衙門象徵的旗桿,並把巡撫趕走。過後,布政使騎著馬出來了。他告訴老百姓,政府準備設法救濟他們。他這話顯然是誠懇的。但皇帝(或許是慈禧太后吧)不高興他,責備他與“暴徒”發生密切關係,並將他撤職。一位新巡撫來了,馬上下令捉拿為首的亂黨。其中有許多人被砍卻頭顱,掛在柱子上示眾。
這事件,我們在私塾裏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予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學生都同情“亂黨”,但祗是站在旁觀的立場。他們並不瞭解這對於他們的生活(有)(14)什麼關係。他們不過把這事當做一個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記它。我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良民,於是我深恨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了。
此後不久,“哥老會”(全國聞名的一種秘密結社)的會員和當地的一個地主發生衝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會員,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地主,判決自然是有利於他的。“哥老會”會員失敗了。但是他們並不屈服,他們向這個地主和政府反抗,他們退到一個山(15)上去,在那裏建築了他們的山寨。官兵派來打他們,同時那地主散佈一個謠言,說他們揭竿造反的時候殺死了一個孩童來祭旗。當時叛徒的領袖叫做“磨刀石彭”(16)。叛徒最後戰敗,彭被迫逃亡。結果他被捕砍頭。然而在我們這般學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造反。
第二年,新穀還沒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發生食糧恐慌。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動了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他不顧本村缺少糧食,將許多米由我們的鄉村運到城裏。其中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他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我以為村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發生影響,即一個小學校中有一個“激烈”的教員。他之所以被目為“激烈”,是因為他反對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廟宇改為學校。他成為一個被大家議論的人。然而我欽慕他,並同意他的意見。
這些密切發生在一起的事件,給予我這已經有著反叛性的青年頭腦以一個永久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識,尤其是在我讀了一個談論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之後。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子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它講到日本的佔領高麗與臺灣,中國的失去安南、緬甸等。(17)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我為我祖國的將來痛心,開始明瞭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
我的父親要我在一個與他有關系的米店做學徒。最初我並不反對,以為這也許是很有趣的。但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一個有趣的新學校。於是不顧我父親的反對,立志進那個學校。這學校在我外祖母的縣城裏(18)。我的一個姨表在那裏當一個教員(19),他將這個學校告訴我,並將“新法”學校的變遷情形講給我聽。那裏是不大注重經書的,西方的“新知識”教授得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進”的。
於是我與我的另一個表弟進了那個學校,注了冊(20)。我自稱為湘鄉人,因為我知道那學校祗收湘鄉籍學生。但後來我發現各地人都可以進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貫說出來,我付了十四吊銅板,做我五個月的膳宿費及購買各種文具用品之用。我的父親終於讓我入學了,因為朋友勸他,說這種“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離家有五十裏。這時我是十六歲。
在這個新學校中,我讀到了自然科學和西洋學術的新課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員中有一位日本留學生,他戴了一個假辮子。假辮子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每個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未看見過那麼多的兒童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著華麗的衣服;很少有農民能將他們的子弟送到那樣一個學校去讀書。我穿得比旁的學生都蹩腳。我祗有一套像樣的襖褲。一般學生是不穿長袍的,祗是教員穿,至於洋裝,祗有“洋鬼子”才穿。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我常穿破爛的襖褲。但是,在這些人之中我也有幾個朋友,而且有兩個是我的好同志。其中有一個現在成了作家,住在蘇聯。
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又不為人所喜。做一個湘鄉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鄉的某一區人也很重要。湘鄉分為上區、中區,與下區,上區的學生與下區的學生不斷地打架,完全是因為鄉土觀念。雙方好像要拼個你死我活似的。在這“戰爭”中,我總是採取中立地位,因為我不是那一區的人。結果三區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覺十分苦痛。
我在這學校裏有很大的進步。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為我古文作得不錯。然而我的志趣並不在經書。我正在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本關於康有為改革運動的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夠背誦出來。我很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並十分感激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非常前進(進步)(21)的,但後來他變成了一個反革命分子,變成一個劣紳,並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大革命時代參加反動工作。
許多學生不歡喜“假洋鬼子”,因為他的辮子是假的,但我很歡喜聽他談日本的情形。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過一個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記得當中幾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何等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青,
正是一幅新鮮的圖畫。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又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它對於戰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揚。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野蠻的日本。
這一切,都是我從“假洋鬼子”那裏學到的。
我又記得在這個時候,在新皇宣統[溥儀]已統治了兩年的時候,我才最初聽到皇帝[光緒]與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時我還沒有成為一個反君主的人。老實說,我認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誠實、良好,和聰明的人。他們祗需要康有為的變法就行了。我心醉於中國古代的著名君主——堯舜、秦始皇、漢武帝的史實,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籍。同時,我還讀了一點外國的歷史和地理。在一篇論美洲革命的文章裏,我初次聽到美國,記得文中有這樣一句:“八年之苦戰後,華盛頓勝利而造成其國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傳》的書中,我又讀到,拿破崙,俄國喀德琳[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登[惠靈頓],葛拉德斯吞[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及林肯。(22)
我開始渴想到長沙去,那是一個大城市,是湖南的省會,離我家有一百四十裏,我聽說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許許多多居民,許多學校和一個巡撫的衙門。這簡直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時我很想到那裏去,進那個為湘鄉人辦的中學。是年冬,我請求我在高小時的一位教員介紹我前去。他答應了,於是我步行到長沙,心中極端地興奮,一半生怕被摒,幾乎不敢希望真入那個偉大的學校做一學生。而使我驚異的,我很容易地就錄取了。但是政局變動得很厲害,我在那裏祗讀了半年。
附註:
(1)據《西行漫記》載,毛澤東的父親叫毛順生,母親“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2)據《西行漫記》載:“他當了好多年的兵。”
(3)據《西行漫記》載:“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穀的剩餘。”
(4)括弧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5)括弧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所加。
(6)據《西行漫記》載:“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
(7)史諾即埃德加-斯諾。括弧內文字是斯諾筆錄時附註的。
(8)括弧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9)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0)《西行漫記》載:“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
(11)括弧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2)括弧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3)括弧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4)括弧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加。
(15)據《西行漫記》載,這個山叫“瀏山”。
(16)據《西行漫記》載:“起義的領袖,是一個叫彭鐵匠的人。”
(17)據《西行漫記》載:“這本書談到了日本佔領朝鮮、臺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
(18)即湘鄉縣。編者註。
(19)據《西行漫記》載:“我的一個表兄就在那裏上學。”
(20)據《西行漫記》載:“我隨表兄到那所學堂去報了名。”
(21)括弧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校訂。
(22)此段括弧內文字均根據《西行漫記》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