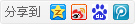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一月十八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要討論的問題主要是三個: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經濟問題。今天我講一講思想動向問題。
思想動向問題,我們應當抓住。這里當作第一個問題提出來。現在,黨內的思想動向,社會上的思想動向,出現了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有一種問題是我們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現在有些干部爭名奪利,唯利是圖。在評級過程中,有那樣的人,升了一級不夠,甚至升了兩級還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級才起床。他這么一鬧,就解決了一個問題,什么干部評級,根本不評了,工資大體平均、略有差別就是了。以前北洋軍閥政府里有個內閣總理,叫唐紹儀,后頭當了廣東中山縣的縣長。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么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我看,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他們不是比艱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闊氣,比級別,比地位。這類思想在黨內現在有很大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農業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是合作社好,還是個體經濟好?,這個問題也重新提出來了。去年這一年,豐收的地方沒有問題,重災區也沒有問題,就是那種災而不重、收而不豐的合作社發生了問題。這類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許的愿大了,后頭沒有那么多,社員收入沒有增加,甚至還有減少。于是議論就來了:合作社還好不好,要不要?這種議論也反映到黨內的一些干部中間。有些干部說,合作社沒有什么優越性。有些部長到鄉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氣不妙,說是農民無精打采,不積極耕種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潰滅亡之勢。有些合作社社長抬不起頭來,到處挨罵,上面批評,報紙上也批評。有些黨委的宣傳部長不敢宣傳合作社的優越性。農業部的部長廖魯言,又是黨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據他講,他自己泄了氣,他下面的負責干部也泄了氣,橫直是不行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不算數了。泄了氣怎么辦?這個事情好辦,你沒有氣,給你打點氣就是了。現在報紙上的宣傳轉了一下,大講合作社的優越性,專講好話,不講壞話,搞那么幾個月,鼓一點氣。
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進”的結果又出了個右傾。我說的這個右傾,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我們的干部中間刮起了這么一股風,象臺風一樣,特別值得注意。我們的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的干部中,相當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爺是地主,現在還沒有選舉權。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講那么一些壞話,無非是合作社不行,長不了。富裕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層,他們的單干思想現在又在抬頭,有些人想退社。我們干部中的這股風,反映了這些階級和階層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兩年內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黨、政、軍、民各界的同志們講清楚。合作社只有這么一點歷史,大多數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歷史,經驗很少。搞了一輩子革命的人還會犯錯誤,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點錯誤都不犯呢?一有點風,有點雨,就說合作化不行了,這種思想本身就是個大錯誤。事實上,多數合作社是辦得好的和比較好的。只要拿出一個辦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對合作化的一切怪論打下去。為什么這個社能辦好,別的社就不能辦好?為什么這個社有優越性,別的社就沒有優越性?你就到處大講這個社的經驗。一個省總可以找出這樣一個典型嘛!要找那個條件最差,地勢不好,過去產量很低,很窮的社,不要找那個本來條件就好的社。當然,你搞幾十個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個,就算勝利。
在學校里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進行煽動, 組織示威游行, 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他們提出的口號那樣反動,工人不同情,農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眾都不同情。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同志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幾萬人,我們就要專政。
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的地主、富農,城市里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幾萬人。對于他們的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因為他們沒有本錢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不聽他們的,他們腳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變,一個原子彈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爛,這些人不起變化呀?那就難說了。那時,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都要分化。他們老于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么“要殺幾千幾萬人”、什么“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么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里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征“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以后,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蘇共“二十大”一來,有些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人,這時候也反得很積極。我看這些人不講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問題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包括無產階級的革命道德。你從前那么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斯大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國黨都牽涉到了。
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干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林整得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臺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么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后頭帝國主義幾棍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幾棍子,連赫魯曉夫的腔調都不得不有所改變,他們又搖過來了。大勢所趨,不搖過來不行。墻上一南草,風吹兩邊倒。搖過來不是本心,搖過去才是本心。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
臺風一刮,動搖分子擋不住,就要搖擺,這是規律。我勸大家注意這個問題。有些人搖那么幾次,取得了經驗,就不搖了。有那么一種人,是永遠要搖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類作物,因為稈子細,風一吹就要搖。高粱、玉米比較好些,稈子比較粗。只有大樹挺立不拔。臺風年年都有,國內國際的思想臺風、政治臺風也是年年都有。這是一種社會的自然現象。政黨就是一種社會,是一種政治的社會。政治社會的第一類就是黨派。黨是階級的組織。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主要是由工人和半無產階級的貧農出身的人組成的。但是,也有許多黨員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他們中間有相當多的人,雖然艱苦奮斗多少年,有所鍛煉,但是馬克思主義學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還是跟稻子一樣,風一吹就要搖。
有些黨員,過去各種關都過了,就是社會主義這一關難過。有這樣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個。她原來是河北省的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她是什么時候動搖的呢?就是在開始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統購統銷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步驟。她卻堅決反對,無論如何要反對。還有一個,就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孟用潛。他上書言事,有信一封,也堅決反對統購統銷。實行農業合作化,黨內也有人起來反對。總而言之,黨內有這樣的高級干部,他們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是動搖的。這類事情結束沒有呢?沒有。是不是十年以后這些人就堅定起來,真正相信社會主義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問題,他們還可能說,我早就料到了的。
發給同志們一個材料,是反映某些軍隊干部的思想動向的。這些干部的意見中雖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說有些干部的工資太高,農民看不慣,但是,他們的意見總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線不對。他們批評我們黨的政策是農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國雖然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兩塊地方,一塊叫農村,一塊叫城市。照他們這一講,都錯了。
所謂農村政策“左”了,就是說農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農民多,但是他們生產的價值比農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農民多。農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農民自己努力發展生產。政府也大力幫助農民,比如興修水利,發放農貸,等等。我們的農業稅,包括副業的稅收,約占農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業沒有抽稅。我們統購糧食,是按照正常的價格。國家在工業品和農業品交換中間從農民那里得到的利潤也很少。我們沒有蘇聯那種義務交售制度。我們對于工農業產品的交換是縮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蘇聯那樣擴大剪刀差。我們的政策跟蘇聯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說我們的農村政策“左”了。
在我們軍隊的高級干部中間,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親屬來,聽到富裕中農、富農、地主的那些話,受了觸動,于是就替農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黨內有相當多的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應,好象只有他們這兩部分人才代表農民,才知道農民的疾苦。至于我們黨中央,在他們看來,那是不代表農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黨員的大多數都是不代表的。江蘇作了一個調查,有的地區,縣區鄉三級干部中間,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農民叫苦。后頭一查,這些替農民叫苦的人,大多數是家里比較富裕,有余糧出賣的人。這些人的所謂“苦”,就是有余糧。所謂“幫助農民”、“關心農民”,就是有余糧不要賣給國家。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誰呢?他們不是代表廣大農民群眾,而是代表少數富裕農民。
至于說城市政策右了,看起來也有點象,因為我們把資本家包了下來,還給他們七年的定息[1]。七年以后怎么辦?到時候還要看。最好留個尾巴,還給點定息。出這么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政策,中央是仔細考慮過的。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里,而在我們手里。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干凈,沒有剝奪干凈的還要剝。所以,也不能說我們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們的農村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確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無非是少數人這里鬧一下,那里鬧一下,要搞所謂大民主。大民主也沒有什么可怕。在這個問題上,我跟你們不同,你們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說來一個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么,做什么。那些壞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殺幾千幾萬人”,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嗎?能得到大多數人同情嗎?“打倒法西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公然違反憲法嗎?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有優越性,這都是憲法里頭講了的,是全國人民公認的。“要戰爭不要和平”,那好呀!你來號召戰爭,統共那么幾個人,你的兵就不夠,軍官也沒有訓練好。這些娃娃們發瘋了!石家莊那個學校,把那三個口號一討論,七十個代表,只有十幾個人贊成,有五十幾個人反對。然后,又把這幾個口號拿到四千學生里頭去討論,結果都不贊成,這十幾個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堅持這幾個口號的極反動分子,只有幾個人。他們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干什么。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沖,黨政軍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亂子,那個膿包就好解決了,這是好事。帝國主義,我們從前不怕,現在也不怕。我們也從來不怕蔣介石。現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我們敢于改造資本家,為什么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于對它進行鑒別和斗爭。田里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雜草年年要鋤,一年要鋤幾次。你說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長糧食,不能長一根草。話盡管那樣講,凡是到田里看過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動手鋤,草實際上還是有那么多。雜草有個好處,翻過來就是肥料。你說它沒有用?可以化無用為有用。農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雜草作斗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斗爭。所謂鍛煉出來的,就是奮斗出來的。你草長,我就鋤。這個對立面是不斷出現的。雜草一萬年還會有,所以我們也要準備斗爭一萬年。
總而言之,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講話
現在,我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要足夠地估計成績。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也有。有那么多成績,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這個問題,本來八屆二中全會已經解決了,這次會上還多次談到,可見在一些同志思想上還沒有解決。特別在民主人士里頭有一種議論:“你們總是講成績是基本的,這不解決問題。誰不知道成績是基本的,還有缺點錯誤呀!”但是,確實成績是基本的。不肯定這一點,就泄氣。對合作化就有泄氣之事嘛!
第二點,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采取這個方針。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報》作社評一篇,說什么不要“另起爐灶”。重慶談判期間,我對《大公報》的負責人講,你那個話我很贊成,但是蔣委員長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么辦?那個時候,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要各得其所。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包括把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都包下來,連跑到臺灣去的也可以回來。對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殺的,都加以改造,給生活出路。民主黨派保留下來,長期共存,對它的成員給予安排。總而言之,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比如統購統銷,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里頭的缺糧戶,我們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這是一個什么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這種統籌兼顧的思想,要向大家說清楚。
柯慶施[2]同志講,要想盡一切辦法。這個話很好,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解決困難。這個口號應當宣傳。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萬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總要好一點吧。長征途中,在過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統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們那個時候提出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什么叫千方百計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計者,就是九十九計加一計。現在你們還沒有提出幾個方幾個計來。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計呀?只要想盡一切辦法,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第三點,國際問題。在中東,出了一個蘇伊士運河事件。一個人,叫納賽爾,把運河收歸國有了;另外一個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著,第三個人,叫艾森豪威爾,要趕走英國人,把這個地方霸起來。英國資產階級歷來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的一個階級。現在它把中東搞到美國人手里去了。這個錯誤可大啦!這樣的錯誤,在它歷史上數得出多少呀?這一回為什么沖昏頭腦犯這個錯誤呢?因為美國壓得太兇,它沉不住氣,想把中東奪回去,阻止美國。英國的矛頭主要是對埃及的嗎?不是。英國的文章是對付美國的,美國是對付英國的。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當前世界斗爭的重點。當然,帝國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是很厲害的矛盾,但是,他們現在是假借反共產主義之名來爭地盤。爭什么地盤呢?爭亞洲非洲十億人口的地盤。目前他們的爭奪集中在中東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特別是埃及蘇伊士運河地區。在那里沖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現在帝國主義爭奪的主要場所是亞洲非洲。在這些地區都出現了民族獨立運動。美國采用的辦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東就是這樣。
他們鬧,對我們有利。我們的方針應當是,把社會主義國家鞏固起來,寸土不讓。誰要我們讓,就一定要跟他斗爭。出了這個范圍,讓他們去鬧。那末,我們要不要講話呢?我們是要講話的。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我們就是要支持。
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支持他們那里的人民革命,他們在我們這里搞顛覆活動。他們里頭有我們的人,就是那里的共產黨,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進步人士。我們里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還有地主階級。現在這些人看起來還聽話,還沒有鬧事。但是假使原子彈打到北京來了,他們怎么樣?不造反呀?那就大成問題了。至于那些勞改犯,石家莊那個學校鬧事的領袖人物,北京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消化掉,要把地主、資本家改造成為勞動者,這也是一條戰略方針。消滅階級,要很長的時間。
總之,對于國際問題的觀察,我們認為還是這樣:帝國主義之間鬧,互相爭奪殖民地,這個矛盾大些。他們是假借跟我們的矛盾來掩蓋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矛盾,這里很有文章可做。這是關系我們對外方針的一件大事。
講一講中美關系。我們在會上印發了艾森豪威爾給蔣介石的信。我看這封信主要是給蔣介石潑冷水,然后又打點氣。信上說需要冷靜,不要沖動,就是說不要打仗,要靠聯合國。這是潑冷水。蔣介石就是有那么一點沖動。打氣,就是說要對共產黨繼續采取強硬的政策,還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出亂子上。在他看來,亂子已經出了,共產黨是沒有辦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觀察吧!
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系為好。這比較有利。蘇聯跟美國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持續到一九三三年。這一年,德國是希特勒上臺,美國是羅斯福上臺,這個時候,蘇美才建交。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于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于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采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于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各國很不穩定,亂,人心不安。世界各國都不安,中國也在內。但是,我們總比他們安一點。你們研究一下看,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美國之間,究竟誰怕誰?我說都怕。問題是誰怕誰多一點?我有這么一個傾向:帝國主義怕我們多一點。作這樣的估計也許有個危險,就是大家都睡覺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帝國主義是不懷好心的,總是要搗鬼的。當然,現在帝國主義要打世界大戰也不那么容易,打起來的結果如何,他們要考慮。
再講一講中蘇關系。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斗爭的。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爭。現在中蘇之間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們想問題做事情的方法,他們的歷史習慣,跟我們不同。因此,要對他們做工作。我歷來說,對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說,既然都是共產黨員,就應當一樣好,為什么還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統一戰線,做民主人士的工作,為什么還要做共產黨員的工作呀?這種看法不對。共產黨里頭還是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組織上進了黨,思想上還沒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們的語言也不一致。所以,經常要談心,要個別商談或者集體商談,要開多少次會,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據我看,形勢比一些人強,甚至比大官強。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就給他們捅穿了一些問題。我在電話里跟恩來同志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什么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么?這叫不算數。看見這么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么共產黨員,什么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當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則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當了第一書記,也是一種利,也容易使頭腦發昏。昏得厲害的時候,就得用一種什么辦法去臭罵他一頓。這回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抬杠子了,搞得他們也抬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法寶不一次使用干凈,手里還留了一把。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那些不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
在我們自己方面,對外宣傳不要夸大。無論什么時候,都要謙虛謹慎,把尾巴夾緊一些。對蘇聯的東西還是要學習,但要有選擇地學,學先進的東西,不是學落后的東西。對落后的東西是另一種學法,就是不學。他錯誤的東西,我們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個錯誤。他那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一定要學。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
第四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在批判了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后提出來的,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證法的。
關于辯證法,列寧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于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2]解釋和發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要解釋,我們現在解釋太少了。還要發展,我們在革命中有豐富的經驗,應當發展這個學說。列寧還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3]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
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丑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
在哲學里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這兩個東西是相互斗爭的。還有兩個東西,叫做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也是對立統一、相互斗爭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蘇聯現在不搞對子,只搞“單干戶”,說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中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存在。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有唯心主義,都有形而上學,都有毒草。蘇聯那里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那里的許多怪議論,都戴著唯物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帽子。我們公開承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香花和毒草的斗爭。這種斗爭,要永遠斗下去,每一個階段都要前進一步。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這樣。他們努力學習和研究當代的和歷史上的各種東西,并且教人們也這么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在研究資產階級的東西,研究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并且跟它們作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斯大林就比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個時期,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說成是德國貴族對于法國革命的一種反動。作這樣一個結論,就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全盤否定了。他否定德國的軍事學,說德國人打了敗仗,那個軍事學也用不得了,克勞塞維茨[4]的書也不應當讀了。
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并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他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征。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系,好像無緣無故什么東西都是聯系的。究竟是什么東西聯系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系。各種事物都有對立的兩個側面。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斗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系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
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于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系,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轉化到戰爭。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5]和平時期的斗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么突然來一個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為什么突然來一個和平?
生與死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地球上原來只有無生物,生物是后來才有的,是由無生物即死物轉化而來的。生物都有新陳代謝,有生長、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動的過程中,生與死也在不斷地互相斗爭、互相轉化。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轉化,為什么經過革命,無產階級變為統治者,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比如,我們和蔣介石國民黨就是根本對立的。對立雙方互相斗爭、互相排斥的結果,我們和國民黨的地位都起了變化,他們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我們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逃到臺灣去的國民黨不過十分之一,留在大陸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來的這一部分,我們正在改造他們,這是在新的情況下的對立統一到臺灣去的那十分之一,我們跟他們還是對立統一,也要經過斗爭轉化他們。
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我們堅持對立統一的觀點,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放出來。這并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
有些現象在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以后就有辦法了。比如,過去把劇目控制得很死,不準演這樣演那樣。現在一放,什么《烏盆記》、《天雷報》,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戲臺上來了。這種現象怎么樣?我看跑一跑好。許多人沒有看過牛鬼蛇神的戲,等看到這些丑惡的形象,才曉得不應當搬上舞臺的東西也搬上來了。然后,對那些戲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說,有的地方戲不好,連本地人也反對。我看這種戲演一點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腳站不住腳,還有多少觀眾,讓實踐來判斷,不忙去禁止。
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么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對于一些有害的言論,要及時給予有力的反駁。比如《人民日報》登載的《說“難免”》那篇文章,說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并不是難免的,我們是用“難免”這句話來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一個對臺戲。我們搞革命和建設,總難免要犯一些錯誤,這是歷史經驗證明了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就是個大難免論。我們的同志誰愿意犯錯誤?錯誤都是后頭才認識到的,開頭都自以為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我們不要因為錯誤難免就覺得犯一點也不要緊。但是,還要承認工作中不犯錯誤確實是不可能的。問題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會上的歪風一定要打下去。無論黨內也好,民主人士中間也好,青年學生中間也好,凡是歪風,就是說,不是個別人的錯誤,而是形成了一股風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辦法就是說理。只要有說服力,就可以把歪風打下去。沒有說服力,只是罵幾句,那股歪風就會越刮越大。對于重大問題,要作好充分準備,在有把握的時候,發表有充分說服力的反駁文章。書記要親自管報紙,親自寫文章。
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斗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義上,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一個原子分兩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電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電子很輕,一個電子大約只有最輕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過結合得比較牢固。電子可有些“自由主義”了,可以跑掉幾個,又來幾個。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也是對立統一,有主有次。從這樣的觀點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有益無害的了。
第五點,鬧事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
社會上的事情總是對立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對立統一的,有人民內部的對立統一,有敵我之間的對立統一。在我們的國家里還有少數人鬧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會上仍然有各種對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對立的階級,對立的人們,對立的意見。
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們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會上還有那樣的人,罵我們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們的省委根本就沒有死,怎么僵呢?罵省委是“僵尸”跟我們說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對立的。
在我們黨內,也有各種對立的意見。比如,對蘇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對和擁護兩種對立的意見。黨內的不同意見是經常發生的,意見剛剛一致,過一兩個月,新的不同意見又出來了。
在人們的思想方法方面,實事求是和主觀主義是對立的。我看那一年都會有主觀主義。一萬年以后,就一點主觀主義都沒有呀?我不相信。
一個工廠,一個合作社,一個學校,一個團體,一個家庭,總之,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時候,都有對立的方面。所以,社會上少數人鬧事,年年都會有。
對于鬧事,究竟是怕,還是不怕?我們共產黨歷來對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不怕,現在倒怕學生鬧事,怕農民鬧社,這才有點怪哩!對群眾鬧事,只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蘇聯也有些人怕。我們對于少數人鬧事,應當采取積極態度,不應當采取消極態度,就是說不怕,要準備著。怕是沒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來。不怕鬧,有精神準備,才不致陷于被動。我看要準備出大事。你準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準備出大事,亂子就出來了。
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么辦?大家就嗚呼哀哉,痛哭流涕?當然,我們現在并沒有打算回延安,來個“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于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發生少數人鬧事,有些是由于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再一個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存在。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這又是個難免論。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線錯誤,全國性的大亂子是不會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線錯誤,出了全國性的亂子,我看也會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國。當然,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歷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皇帝,來了軍閥。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國性的大亂子,那時總會有群眾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來收拾時局,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別人。經過那樣一次大亂子,膿包破了以后,我們的國家只會更加鞏固。中國總是要前進的。
對于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并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于收場,總有一天他還是要鬧。凡有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硬是來它一場赤壁鏖兵。這有什么好處呢?就是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
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么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對于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并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后退,毫無原則,什么要求都答應。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
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我看什么地方都是兩頭小中間大。要把中間派一步一步地爭取過來,這樣,我們就占優勢了。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面教員。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志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里很干凈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于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蘇聯大學生鬧事,他們就開除幾個領袖人物,他們不懂得壞事可以當作教材,為我們所用。當然,對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斗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對壞人壞事的斗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將在斗爭中取得經驗,受到鍛煉,這是很有益處的。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壞事里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只看成壞,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面是壞,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面教員的好作用。同樣,好事里頭也包含著壞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來的大勝利,特別是去年這一年的大勝利,使有些同志腦筋膨脹,驕傲起來了,突然來了個少數人鬧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
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他以為他那個天下穩固了。我們不要以為天下穩固了,它又穩固又不穩固。
按照辯證法,就象人總有一天要死一樣,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總有一天要滅亡,要被共產主義制度所否定。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不會滅亡的,那還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那不是跟宗教教義一樣,跟宣傳上帝不滅亡的神學一樣?
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斗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如果一萬年以后地球毀滅了,至少在這一萬年以內,還有鬧事的問題。不過我們管不著一萬年那么遠的事情,我們要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認真取得處理這個問題的經驗。
要加強我們的工作,改正我們的錯誤和缺點。加強什么工作呢?工、農、商、學、兵、政、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現在大家搞業務,搞事務,什么經濟事務,文教事務,國防事務,黨的事務,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險。現在我們的總書記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馬到清華大學作報告,也請你們大家都出馬。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同志,都要親自出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蘇聯共產黨,東歐一些國家的黨,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黨與群眾的聯系,這些他們都不講了,空氣不濃厚了。結果出了個匈牙利事件。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每個省市自治區都要把理論工作搞起來,有計劃地培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評論家。
要精簡機構。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階級不等于國家,國家是由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出一部分人(少數人)組成的。機關工作是需要一點人,但是越少越好。現在國家機構龐大,部門很多,許多人蹲在機關里頭沒有事做。這個問題要解決。第一條,必須減人;第二條,對準備減的人,必須作出適當安排,使他們都有切實的歸宿。黨、政、軍都要這樣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問題。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區、各部的主要負責同志都這樣做。聽說現在許多負責同志不下去了,這不好。中央機關苦得很,在這個地方一點知識也撈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識,蹲在機關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識的地方是工廠、合作社、商店。工廠怎么辦,合作社怎么辦,商店怎么辦,在機關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層越沒有東西。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請下面的人上來。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請下面的人上來,就不能解決問題。我建議,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兼一個縣委書記,或者兼一個工廠或學校的黨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要兼一個下級單位的書記。這樣可以取得經驗,指導全局。
要密切聯系群眾。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領導人,沒有調查研究,不了解群眾情況,等到大亂子出來了,還不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現在我們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不了解群眾的思想動態,有人醞釀鬧事,醞釀暴動,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們一定要引為鑒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區、各部的主要負責同志,一年總要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等基層單位去跑一跑,進行調查研究,搞清楚群眾的情況怎樣,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們的群眾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數。要依靠工人階級,依靠貧農下中農,依靠先進分子,總要有個依靠。這樣,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樣的事件。
第六點,法制問題。講三條: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肅反,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層建筑。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肅反。沒有完成肅反計劃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點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單位進行過肅反,但是肅而不清,必須在斗爭中逐步肅清。反革命不多了,這一點要肯定。在鬧事的地方,廣大群眾是不會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暫時的。同時也要肯定,還有反革命,肅反工作沒有完。
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肅反的成績是偉大的。錯誤也有,當然要嚴肅對待。要給做肅反工作的干部撐腰,不能因為一些民主人士一罵就軟下來。你天天罵,吃了飯沒有別的事做,專做罵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罵越好,我講的這三條總是罵不倒的。
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別人跟我們通,就叫“通匪”。結果,還是“匪”比他們非“匪”好。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一萬年以后,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
肅反要堅持,有反必肅。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辦事,不等于束手束腳。有反不肅,束手束腳,是不對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腳。
第七點,農業問題。要爭取今年豐收。今年來一個豐收,人心就可以穩定,合作社就可以相當鞏固。在蘇聯,在東歐一些國家,搞合作化,糧食總要減產多少年。我們搞了幾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沒有減產,而且還增產了。如果今年再來一個豐收,那在合作化的歷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就是沒有先例的。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 要 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首先,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 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第二,農業也關系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
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為農業服務。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
第五,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第六,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
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臺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
總之,要照辯證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我看,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斗爭中的新問題。
注釋
(1)定息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國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政策的一種形式。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國家按照資本家的資產,在一定時期內,每年付給他們固定息率的股息,叫做定息。定息仍然屬于剝削的性質。
(2)見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3)見列寧《關于辯證法問題》。
(4)克勞塞維茨(一七八○——一八三一),著名的德國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家,主要著作有《戰爭論》。斯大林對克勞塞維茨的評論,參看斯大林《給拉辛同志的復信》。
(5)見列寧《戰爭與革命》。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0--3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