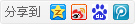第03章 揭開紅史的第一頁
一九二〇年夏,我赴滬參加會議,共產黨就在這個會議上成立。(42)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中,陳獨秀和李大釗佔著領導的地位,無疑地,他們都是中國知識界中最燦爛的領袖。
我在李大釗手下做圖書館佐理員時,已經很快地傾向馬克思主義了,而陳獨秀對於引導我的興趣到這方面來,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赴滬時,我曾和陳獨秀討論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本人信仰的堅定不移,在這也許是我一生極重要的時期,給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這個歷史的上海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以外,祗有一個湖南人。參加會議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產黨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其中的一員。當時在其他省縣中也有組織成立……(43)同時,在法國,許多工讀生組織了一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組織幾乎同時成立……在德國也有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不過較遲,黨員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44)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公務人員、印刷工人及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工會,當時我是支部的書記。是冬,猛烈的勞工運動開始。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學生和工人之間,在農民中的工作極少。多數大礦山和全部學生實際上都已組織起來。在學生和工人的戰線上都有許多鬥爭。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趙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工人領袖(一個叫黃愛,一個叫龐人銓),結果引起了一個廣大的激動,開始反對他。在這兩個被殺的工人中,有一個是右翼勞工運動的領袖(即黃愛)。右翼運動的基礎是工業學校的學生,而且是反對我們的。不過在這一次和許多次其他的鬥爭中,我們援助它。在工會中,無政府主義者也有相當勢力,當時各工會已經組織到“全湘勞工組合”[湖南全省勞工會]裏面。可是,我們和他們妥協,並且用協議的方法阻止了他們許多次魯莽而無用的舉動。(45)
我被派到上海來幫助組織反趙運動。是冬(一九二二年)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會議。我心中想去參加,可是我忘掉開會地點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參加的機會。我回轉湖南,並竭力推動工會的工作。是年春,發生許多次罷工,為了爭取較高的工資、較好的待遇,和爭取工會的承認。多數罷工都是勝利的。五月一日湖南發動了一次總罷工,這件事指出了中國勞工運動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是一九二三年在廣州召開的,通過了那歷史的決議案: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並組織聯合戰線以反對北洋軍閥。我跑到上海去,並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廣州去,並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大會。三月間回滬,將我在共產黨執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國民黨執行部中的工作合併起來。當時部中還有的幾個人,就是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一起工作,調整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步驟。是夏,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加倫(現在叫伐西裏·布留契爾將軍,任蘇維埃遠東紅軍總司令之職)擔任顧問,還有其他從蘇聯來的蘇維埃顧問。國共的合作開始採取一個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是年冬,我回湖南休養——在上海時,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後,我組成了本省偉大農民運動的核心。
在以前我還未充分瞭解農民中階級鬥爭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以後,和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活動的大浪中,湖南農民變成十分地活動了。我利用我所休養的家庭,發動一個農村組織運動,在僅僅幾個月內,我們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農民協會,同時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將我逮捕。趙省長派兵來抓我,我逃到廣州。到達廣州時,黃埔學生剛打敗了兩個著名的軍閥(46),全城和國民黨都充滿了樂觀的空氣。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後,蔣介石先生被任為總司令,汪精衛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週刊》的主編,這是一個國民黨的刊物,後來曾極力攻擊國民黨右翼。我同時又成了訓練農民運動組織者的負責人,並開了一個訓練班來訓練他們。聽講的有二十一個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古來的學生。在我到廣州後不久,我成了國民黨宣傳部的部長。
我寫作越來越多了,同時在共產黨農民工作中負有特殊責任。根據我的研究和在組織湖南農民的工作中所得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中國社會各階層(級)的分析》,另一本叫《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在第一本小冊中,我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施激進的土地政策和積極地組織農民,陳獨秀反對這個意見,並拒絕以共產黨中央機關的名義出版。後來,它在廣州的《農民月刊》和《中國青年》上發表。至於第二本書則是以小冊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這時我開始不滿意陳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漸漸遠離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達到最高峰。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國民黨左右翼和解而國共也重行合作以後,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國民黨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開第二次大會。在上海,我指導著共產黨的農民部,並被派到湖南做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合作之下,於一九二六年秋開始這歷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五個縣份(47)的農民組織和政治狀況,並作就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方面採取新路線。次春初旬,當我抵武漢時,那裏正在舉行各省農民代表會議,我就去參加並討論建議我的主張,即實行廣泛的土地分配。大會決議把我的建議提交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但黨中央將它否決了。
當第五次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召開時,黨還是在陳獨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顧一切地反對,還是堅持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政策。當時我對於黨的政策非常不滿。今日之下,我想假若當時農民運動能更徹底地組織和武裝起來作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麼現在的情勢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國蘇維埃的勢力必定較現在大為強盛。
可是陳獨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見解。他不了解農民在革命中的任務,並將當時農民的前途估計過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機前夜所召開的第五次大會上,不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見,迅速加強土地鬥爭,竟不加以討論,因為黨的中央委員會,也為陳獨秀所把持,拒絕將它提出考慮。大會將“地主”定為擁有五百畝以上的人——要在這種基礎上發展階級鬥爭,是全然不適合和不切實際的,而且忽視了中國土地經濟的特質——這樣就撇開了土地問題。不過,在大會過後,一個“全中國農民協會”組織起來,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48)。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農民運動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發展成為一個驚人的軍事力量,雖然共產黨的態度對它很冷淡。高級官吏和軍事長官開始要求鎮壓它,說農民協會是“流氓協會”(49),它的行動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陳獨秀將我調開湖南,因為那裏發生了幾樁事件,他要我負責,並且猛烈反對我的觀念。
四月間,南京和上海開始了反共的運動。在廣州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一次暴動,有幾十個農人和工人被殺。此後不久國共就分裂了。
許多共產黨領袖現在都奉命離開武漢,到蘇聯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我請求陳獨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員會的書記,但是十天之後,陳命我速回,責備我組織一個反對當時統治湖南的人的運動。(50)黨裏的事務現在是一塌糊塗了。幾乎每個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而國共合作的解體不久也使他沒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和葉挺的部隊,與朱德合作,領導了歷史的“南昌暴動”(51),並組成了後來變成紅軍的第一個部隊。一星期後,八月七日,黨的中央委員會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罷免陳獨秀書記之職。自一九二四年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大會起,我一直是黨的政治局中的人員,並促成了這次決議(罷免陳獨秀)。黨採取了一個新路線,放棄所有合作的希望。開始了長久的公開的爭奪政權的鬥爭。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一個運動,就是後來叫做“秋收暴動”(52)的。我在那裏的計劃是要實現五點:共產黨省黨部完全與國民黨脫離;組織農工革命軍;沒收大中小地主的財產;脫離國民黨,在湖南建立共產黨政權;組織蘇維埃。當時第五點為共產國際所反對,直到後來才進展成為一個口號。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農民協會,我已經組成一個普遍的暴動,並成立農工軍第一隊。我的部隊有三個主要的來源——農民本身,安源的礦工和國民黨中叛變的軍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隊叫做“第一農工軍第一師”(53),是經過省委員會批準後組織起來的。但是湖南省委會的和我部隊的總綱領為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它好像祗採取一種觀望的政策並未作切實的反對。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而僕僕往返於安源礦工及農民自衛軍之間時,我被幾個民團捕獲。那時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槍斃。他們命令將我解到民團總部,要在那裏殺死我。不過,我曾向一個同志借了幾十塊錢,我想用它賄賂護送兵來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傭的兵,他們並沒有特殊的興趣看我被殺,所以他們同意釋放我。但是那個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應,因此我決定還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團總部二百碼的地方才有機會。在這個地點,我掙脫了,跑到田野裏去。我逃到一塊高地,在一個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長的草,我就躲在那裏一直到日落。士兵們追趕我並且強迫幾個農民一同搜尋。好幾次,他們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兩次近得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可是不知怎樣地沒有發現我,雖然有七八次我拋卻希望,覺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後,到了薄暮的時候,他們不搜尋了。我立即爬越山嶺,走了整夜。我沒有鞋子,我的腳傷得很厲害。在路上我碰到一個農民,他和我很要好,給我住宿,隨後又領我到鄰縣去。我身上還有七塊錢,拿它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食物。當我最後安抵農民自衛軍的時候,我的衣袋中祗有兩個銅元了。
隨著第一師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敵委員會的主席,一個武漢軍校的學生成了它的指揮員,不過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態度而不得不就任這個職位的。(54)不久,他就棄職加入國民黨。現在他在蔣介石先生手下,供職南京。
這個小小的軍隊,領導著農民暴動,向湘南移動。它衝破了成千成萬軍隊,作了許多次戰爭,吃了許多次敗仗。當時的軍紀很壞,政治訓練的水準很低,而官兵中有許多動搖分子,所以“開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屆司令逃走後,軍隊改組,剩下來的隊伍約有一團人,換了一個新的司令。後來他(55)也叛變了。但是在最初的團體中有許多人還是忠誠到底,到今天還在軍隊中。(56)當這一小隊人最後爬上井岡山(一個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為盜匪盤據)時,軍隊的數目祗有一千左右了。
因為“秋收暴動”(57)的計劃沒有被中央委員會批準,又因為部隊受了嚴重的損失,同時從城市的觀點看來這個運動好像一定要失敗的,現在中央委員會堅決地排斥我了。將我從政治局和前敵委員會中革出。湖南的省委會也攻擊我,稱我們為“劫掠運動”(58)。可是我們依然帶著我們的軍隊,留在井岡山上,一面確切覺得我們在執行正確的路線,而以後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我們的正確。新的兵士添加進來,這一師又補充起來了。我成為它的司令。
從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師以井岡山為根據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蘇維埃,成立於茶陵,在江西、湖南省邊境上,同時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也選舉出來。(59)在這個蘇維埃,及以後幾年中,我們依據了遲緩但是有規律的發展,建立了一個民主的綱領,伴隨著一個溫和的政策。這使井岡山備受黨中央“盲動主義者”譴責,他們要實施一個恐怖政策,劫掠和殺戮地主並焚燒他們的財產以摧毀他們的膽量。第一師的前敵黨委會拒絕採用這種策略,於是被一般盲動者戴上了“改良主義者”的帽子。我備受他們的攻擊,因為不實行一個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兩個以前盤據井岡山附近的盜魁加入了紅軍。這使我們的力量增加三團左右。這兩個人(60)雖然以前是盜匪,曾率領部下投效國民革命軍,現在更準備與反動勢力鬥爭。當我留在井岡山上的時候,他們始終是忠實的共產主義者,執行黨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後來,到他們單獨留在井岡山時,他們又回復了昔日的強盜脾氣,結果被農民殺死。因為那時他們已經組織起來,已經蘇維埃化,能夠保衛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力量合併起來了。我們共同擬了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六縣的蘇維埃區,我們要穩定和加強湘贛粵三省接境區域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逐漸發展到更廣大的區域中去。這種策略與黨中央辦法相反,他們有著迅速擴展的妄想。在軍隊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與兩種傾向搏鬥:第一,要想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以為是“冒險主義”;第二,要想退到廣東省境之南,這我們以為是“退卻主義”。當時我們的見解,以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權和建立蘇維埃政體。我們要武裝群眾以加速這種過程。我們的政策要實現自由貿易和善遇被俘的敵軍,一句話,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個代表會議在井岡山召開,到會的有井岡山以北的蘇區代表。當時各蘇區的黨員對於上述的政策還存在著幾種不同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這種異點徹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為在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數人信仰這個政策,因此,黨決議提出,宣佈蘇維埃運動一定會勝利的時候,很容易地就通過了。不過黨中央還沒有對這個運動批準。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當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的決議錄的報告到達井岡山時,才得到批準。
關於在那個會上所採取的新路線,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袖和在鄉村中從事蘇維埃運動的領袖間的爭點完全消除,而黨的調和與一致又重新建立起來了。
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綜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經驗,南昌、廣州和秋收暴動的經驗,決定應該強調土地革命運動。這時,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部分出現,賀龍在西面,徐海東在東面,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農工紅軍。同時,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鄰近福建的江西省東北境上,也發動了一個運動,後來並由此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蘇維埃根據地。在“廣州暴動”失敗之後,有一些紅軍部隊都跑到海陸豐去,並在那裏成立了一個蘇維埃,但因為它信奉盲動主義,很快地就被破壞了。一部分部隊從那個區域裏出來,與朱德和我取得聯絡。(61)
當我們在井岡山上“對冒險主義鬥爭”的時期中,我們擊敗了兩次軍隊奪山的企圖。井岡山證明了是我們所建立的這一種流動部隊的絕好根據地。那裏有很好的天然防禦,並出產足夠的收成來供給一個小小的部隊。它的周圍有五百里,直徑約八十裏。在當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個,叫“大小五鎮”(真正的井岡山是附近的一個山)(62)。
山上的情況,因來了這樣多的軍隊,變得十分惡劣了,軍隊沒有冬季制服,食糧也極度稀少。有幾個月,我們簡直靠南瓜過日子,士兵們喊出一個他們自己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盡南瓜!”——因為在士兵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懷在井岡山,我和朱德衝破了軍隊的封鎖,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在這個久經戰陣的山上所造的第一個居留地就算是終結了。
現在紅軍開始在江西一帶作戰,並且順利地迅速發展起來了。我們在閩西建立了一個蘇維埃,並和當地的紅軍聯合起來。我們分出軍力,繼續佔領三縣並建立了蘇維埃。因為在紅軍到達之先,那裏已經有了武裝的群眾運動,這樣,保證了我們的勝利,並且使我們能在一個穩定的基礎上,很快地加強了蘇維埃政權。
附註:
(42)這裏明顯有誤。《西行漫記》記載為:“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
(43)據《西行漫記》載,當時其他黨中央組織有:上海的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李達和李森;湖北的董必武、許白昊、施洋;陝西的高崇裕;北京的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廣州的林伯渠、彭湃;山東的王盡美和鄧恩銘等。
(44)據《西行漫記》載:在法國,黨的創始人有周恩來、李立三、向警予、羅邁和蔡和森;在德國,有朱德、高語罕和張申府;莫斯科支部的創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45)此段括弧內文字為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46)這兩個軍閥即雲南的楊希閔和廣西的劉震寰。新版編者註。
(47)這五個縣即:長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鄉。新版編者註。
(48)在《西行漫記》中,“第一任主席”譯為“第一任會長”。
(49)"流氓協會"在《西行漫記》中譯為“痞子會”。
(50)在《西行漫記》中,此處為:“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
(51)即南昌起義。編者註。
(52)即秋收起義。編者註。
(53)這個軍隊在《西行漫記》中稱做“工農第一軍第一師”。
(54)《西行漫記》中,這個“前敵委員會的主席”譯作“前敵委員會書記”,而那個“武漢軍校的學生”名叫余灑度。
(55)此人叫陳浩。編者註。
(56)例如:羅榮桓、楊立三等將領。編者註。
(57)即秋收起義。編者註。
(58)《西行漫記》譯為“槍桿子運動”。編者註。
(59)據《西行漫記》載,這個蘇維埃政府“主席是杜修經”。
(60)據《西行漫記》載:這兩個人就是王佐和袁文才。王、袁都被任為團長,毛澤東任軍長。
(61)據《西行漫記》載:江西的運動是由方志敏和邵式平領導的;海陸豐的運動是彭湃領導的。“廣州暴動”即“廣州起義”。編者註。
(62)“大小五鎮”在《西行漫記》中稱做“大小五井”,“五井這個名稱是從山麓五口大井得來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個村就是以這五口井相稱”。編者註。